余红芳、王志华、于静亚、沈锦
这四位女园林工程师
都来自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以下简称“市园林科研院植保所”)
平均年龄34岁
每天的工作就是跟虫子打交道
她们是武汉最特别的一个“女团”
人送外号“女子虫虫特攻队”
江城6月各种虫子蠢蠢欲动
她们最繁忙的季节也开始了
记者怀着满满的好奇心
走近了她们的工作和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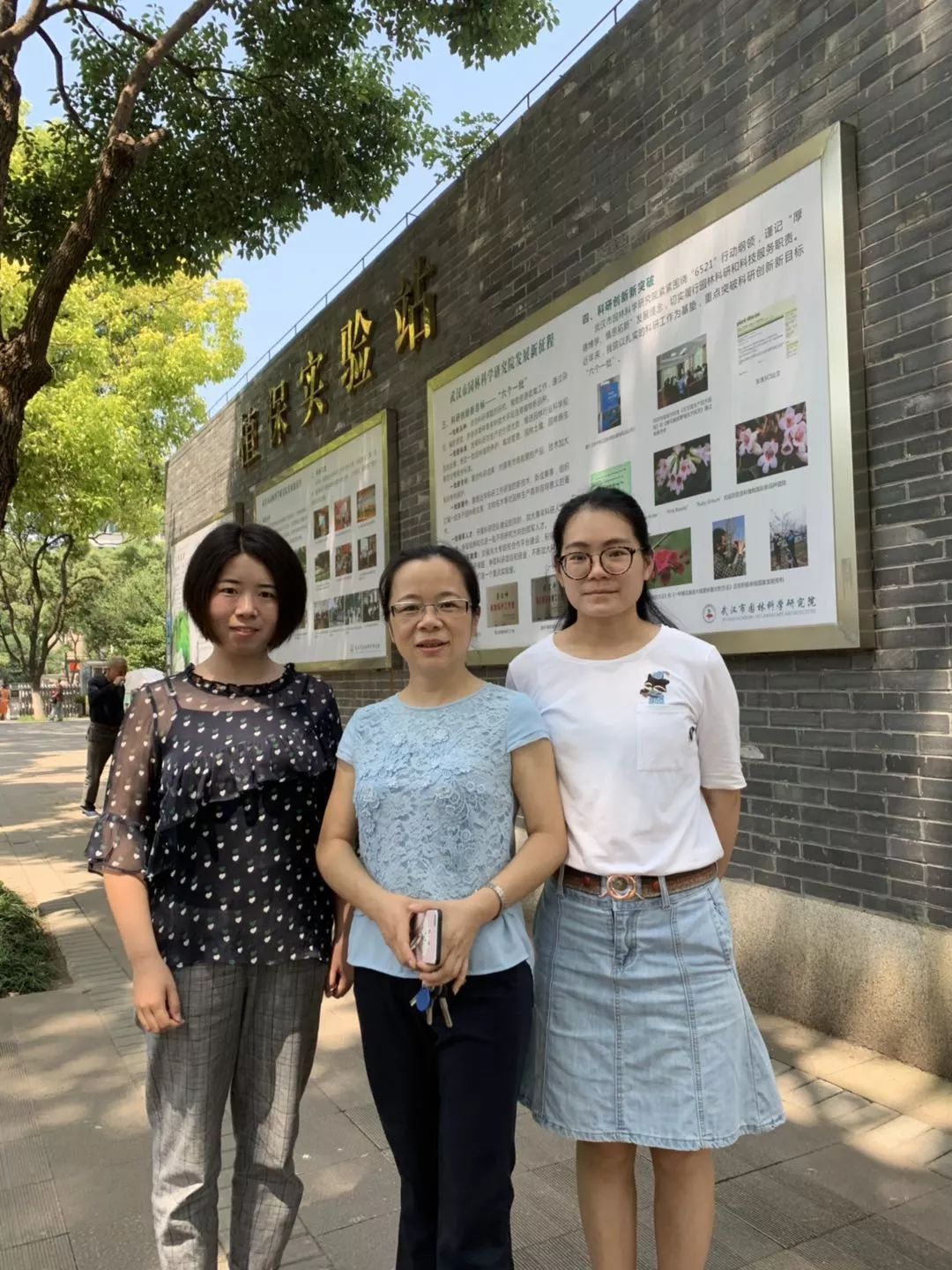
(左起分别为王志华、余红芳、于静亚 贺方程 摄)
她们都有胆
提起虫子,不少女性都会心里犯怵。记者认识的一位90后美眉,连虫子的图片都不敢看。记者虽然不那么害怕虫子,但也不想和它们亲密接触。
6月11日,在市园林科研院植保所的办公室里,于静亚介绍她采集到的虫子标本时,随手拿起一只死去的“大锹甲”展示给记者看,吓得记者后退了一步。

(于静亚展示她采集到的“大锹甲”标本 贺方程 摄)
“你们都不怕虫子吗?”面对记者的疑问,一旁的余红芳笑了。她说女儿就曾问过她,成天跟虫子打交道“恶不恶心”。“你们看到的是虫子,我们看到的就是工作。”她说,“就像在财务的眼里,钱不是钱,钱只是一种符号。”
前几天,她们一起外出做市内新栽大树的病虫监控时,看见树上的虫子,王志华的第一反应就是伸手去抓,想带回来做标本,被余红芳劝阻了。“她没有戴手套,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王志华介绍,她的胆子是在学校上实验课解剖虫子时练出来的。最开始时,她也害怕虫子,尤其是那一类蠕动的虫子。克服了心理障碍后,她甚至觉得一些虫子“很可爱”,比如用来养肿腿蜂的黄粉虫,“白白的,嫩嫩的,很干净”。她也不再用镊子去夹它们,改直接用手去抓。
她们说,只有了解了害虫的生活习性,才能防治。因此,她们在市园林科研院东南角的一个养虫棚里养起了害虫。“单位的同事经常跟我们开玩笑说,你离我远点,你们的害虫不要跑到我的植物上来了。”王志华说。
记者跟随她们来到了这个面积百余平方米的小小养虫棚,棚内种植了一些菊科植物如百日草,还有向日葵、棉花、苘麻等植物。目前主要养了两种害虫:天牛和菊方翅网蝽。余红芳蹲下身来,仔细翻看了几种植物的叶子,跟王志华和于静亚说:“理论上麻天牛取食棉花和苘麻,但咱们这里的情况是,天牛都跑到百日草上面来了。”

(养虫棚里观察虫子 贺方程 摄)
她们都有才
余红芳,市园林科研院植保所所长,理所当然成为“女子虫虫特攻队”的“队长”。除了她是70后,其他三位成员都是80后。她毕业于林业部南京林业学校,读的园林绿化专业,在院里做了十几年的财务工作,后来还是想回归自己的专业,做起了植保工作。目前,正在带头开展武汉市主城区新植大树主要病虫害的监控。

(余红芳在监测树木病虫害 余红芳提供)
“你多写写她们几个年轻人,她们都是名校毕业,工作很出色。”余红芳对记者说。
这支“虫虫特攻队”平时不光承担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控的工作,还要做课题,取得了很多科研成果。
她们中“队龄”最长的是王志华,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2013年加入植保所工作。她在入侵有害生物研究方面成绩斐然,2016年发表的《低温处理黄粉虫蛹对川硬肿腿蜂繁育效果的影响》 ,荣获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植物保护专业委员会优秀论文一等奖。此外,先后在《中国生物防治学报》、《环境昆虫学报》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入侵害虫菊方翅网蝽在中国的潜在分布预测》《不同杀虫剂对外来入侵害虫菊方翅网蝽的毒力测定及防治效果》《花绒寄甲人工繁育及应用研究》。

(王志华在做实验 余红芳提供)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的于静亚,也在生物防治研究方面打开了局面,目前正在研究刺吸类害虫天敌的开发利用。她在2017年发表的《补充营养对延长麦蛾柔茧蜂成虫寿命的影响》,获得了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植物保护专业委员会优秀论文二等奖,还在《植物病理学报》上发表论文《石楠叶斑病病原鉴定及对药物敏感性测定》。

(于静亚在给孩子们讲课 余红芳提供)
刚生完宝宝,目前正在休产假的沈锦,毕业于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刚参加工作不久,就在SCI期刊《Plant Disease》上发表了论文《First Report of Anthracnose Caused by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on Ligustrum japonicum in China》。

(沈锦在做病虫害调查 余红芳提供)
不光如此,她们还承担了科普教学的任务,是真正的“多面手”。于静亚担任过自然研学的自然导师、绿色驿站的讲师,王志华在市民园林学校、市园林科研院的昆虫夏令营、公园大课堂上都讲过课。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五,她们两位还会参与“植物医生”坐诊,为养花市民答疑解惑。
她们都有“劲”
专业、敬业的背后,是“千磨万击还坚劲”。在采访中,她们说说笑笑,把苦事当趣事讲,但记者感受到她们身上都有一股特别能吃苦的“劲”。
江夏安山中试基地是她们常去的地方,因为是野外环境,植物种类多,病虫害种类也多,可以采集更多的标本。路上要花2个多小时。
大热天也要出门。前段时间,武汉气温飙到三十好几,于静亚还去了府河,被晒得快要虚脱了。“武汉最热的时候,40多度也还是要出去的。”她们能做的,就是戴上帽子、口罩和袖套,防止晒伤。

(满满一冰箱的虫子“尸体” 贺方程 摄)
因为长期跟各种虫子亲密接触,皮肤过敏对她们来说是家常便饭。王志华曾经因为对蒲螨过敏,整张脸都红扑扑的。“那些螨虫类的都很小,肉眼看不到,夏天会爬到身上来。原来的实验室没有空调,也不能开风扇,又热又难受。”
余红芳则对有鳞的大蜡螟成虫过敏。又不能因为过敏就把实验停了,“错过了时间就不能观察到我们想知道的东西”,因此大热天的也只好戴着口罩工作。
她们几个还都被肿腿蜂咬过。这种用来对付天牛的虫子,有时会跑到人身上,叮一个包,奇痒无比。
作为她们在植保所唯一的男同事、高级工程师董立坤,更深知她们的不易:“做植保工作很辛苦,对女生来讲更甚。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高温日晒,都要到街头绿地去做现场调查,另外也有课题研究的一些野外调查。在生活中她们还要承担妈妈的角色,带小孩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但她们同时也都在担负着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工作日的晚上和周末加班是经常的事情。”

(“女子虫虫特工队”的办公室 贺方程 摄)
她们都有“病”
因为长期观察虫子研究虫子,她们都有了程度不一的“职业病”。
“我把老公都要搞疯了。”余红芳笑称。前两天,她老公买了一把马齿苋回家准备做菜,她看了一眼,马上叫停:“上面有蚧壳虫,不能吃!”平时择菜,她的第一反应是看菜上有什么虫子。家里的大米、绿豆、黄豆长了绿豆象、印度谷螟等虫子,她都带到实验室里养着,用作科研。
甚至她们的家属也被染上了这种“职业病”。于静亚说,去年夏天她和老公在野外玩的时候,抓到一只“大锹甲”,她老公带回家,用盒子和果冻养了一个月。
王志华则称,家人很支持她的工作,也以她为骄傲。朋友们不认识的花花草草和昆虫,都会用手机拍照发给她帮忙辨认。路上飞过去的蝴蝶,她能准确地说出名字:“那是樟青凤蝶。”她老公常常毫不吝啬地夸她:“老婆好厉害!”

(植保实验站里养的各种虫子 贺方程 摄)
余红芳的女儿目前上初三,因为从小受妈妈熏陶,善于研究,勤于思考,学习成绩优异。多年前,母女俩出去旅游,在哈尔滨太阳岛上,一个同龄的小女孩在对着一朵花赞叹:“啊,好漂亮的红花!”余红芳的女儿就准确地说出了花的名字:“这是芍药花。”
“有时候我们也挺煞风景的。”余红芳笑称。今年春天,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发乡村游的美图,她一眼就看出来:“梨树上长了锈孢子器。”王志华也说,看到朋友在朋友圈发与月季美美的合照,就会善意提醒:与鲜花保持距离,它们得了黑斑病、白粉病,还有农药残留的痕迹。
采访的最后,记者还随她们参观了市园林科研院内的植保实验站。大大小小的房间里,形形色色的的容器中,或生活着各种各样的虫子,或储藏着大小不一的虫子标本。她们如数家珍,向记者一一介绍它们的名字和习性。

(植保实验站里的蝴蝶标本 贺方程 摄)
真不知道,遇上这样一支“虫虫特攻队”,是虫子们的幸还是不幸呢?
(编辑:张轶)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