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聚居在云南怒江地区的傈僳族有自己一年一度的“阔时节”,就相当于汉族的春节,也是傈僳族众多节日中最大的一个。“阔时”是傈僳语的译音,即汉语“岁首”之意。以往的“阔时节”并不固定,以观察自然物候的变化情况来决定,一般选定在每年十二月初五至来年正月初十野桃花开放的季节,前后约一个月,所以这个月又称为“过年月”。1990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自治条例》颁布实施后,把每年的12月20日定为傈僳族“阔时节”的法定节日。
早就听说傈僳族一般不过春节,只是近年来民族交往越来越多,很多习俗也慢慢地影响着傈僳族,因此,在部分傈僳族群众中既过自己的“阔时节”,也过春节。不过,对春节习俗也并未全部接受,也就是在年关来临之际,杀头猪,吃点烤肉,互相走动一下,除夕晚上各个家庭再聚会一下。相比之下,节日气氛远不如“阔时节”,年夜饭也没有汉族的那种仪式感。
既然知道傈僳族一般不过汉族的春节,还兴致勃勃地往傈僳族聚居区跑,目的其实很简单,也就是想了解一下,春节期间,这些兄弟民族在干什么。
一头撞进泸水县鲁掌镇大岩房村实属偶然,进而撞进傈僳族兄弟陆波才的家就更属偶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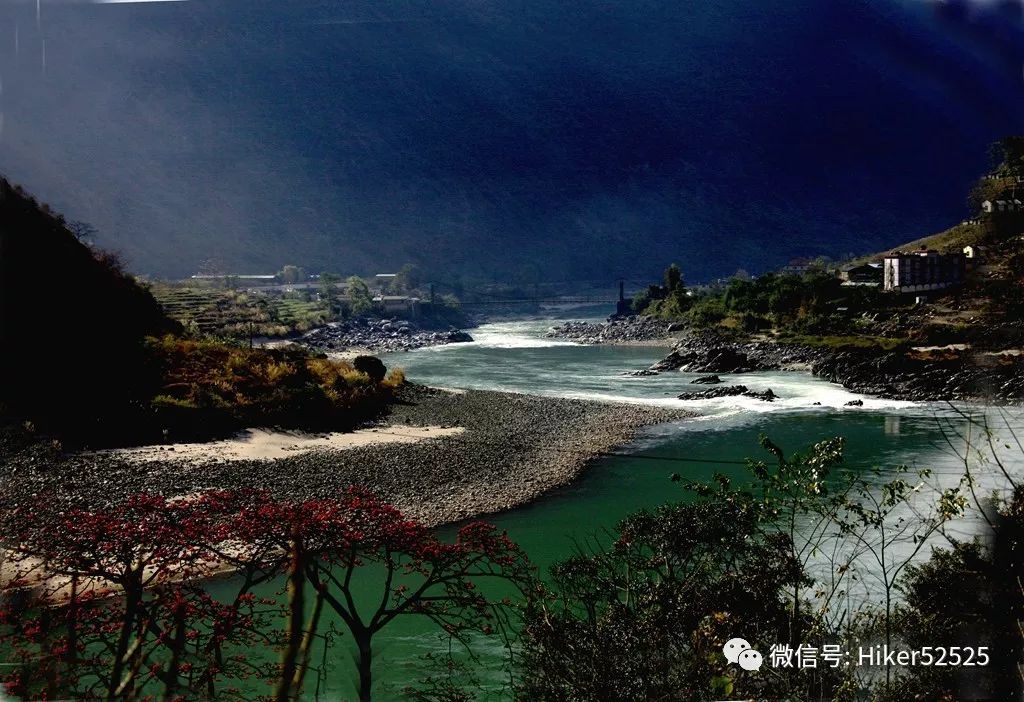
六库镇往北10多公里处有座上世纪1958年建成跨江大桥——跃进桥,这个地名在当地还很响亮。跃进桥附近有个“登埂澡塘”,它的名气就比跃进桥大多了。说是澡塘,请注意“塘”字。此“塘”非彼“堂”,完全不一样。每年的正月初二至初七,附近的傈僳族群众都会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在怒江边的温泉里洗上几天,洗去晦气,洗去病痛,洗出一个清爽的精神世界。
这次去那里有个小目标,就是要找个傈僳人家住下,和他们一起过年,和他们一起沐浴,感受一下网络上遮遮掩掩讲述的“混浴”,体验一把原生态的傈僳族风情。只是出发前并无目标,不知这个傈僳族村寨在何方,也不知那个我要去“蹭饭”的傈僳族人家在哪里。俗话说,两眼一抹黑。
六库出发,车到登埂。远远地看见不远处的半山坡上散落着一个寨子,因为这里是傈僳族聚居区,这个寨子一定是傈僳族村寨。
背着很有些分量的双肩包,顺着山路爬了上去,首先看见的是一座山村教堂。十字架下面“大岩房基督教堂”几个字告诉我,这个傈僳族山寨叫大岩房。
村子里静悄悄的。随着耳旁的阵阵风声,不远处飘来一阵笑声。
我随着笑声传来的方向走了过去。
一栋建筑特色并不鲜明的房屋前的空地上,几个男人正在喝茶聊天。他们对于我这个陌生人的出现似乎并不意外。“坐一下,喝杯茶”,几个男人不约而同。
和素不相识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聊天,这已是我“寻访少数民族风情之旅”的一项基本功了。几句简单的“你们好”之类的问候语,一两个兼顾身边情景的即兴话题,很快就能和他们打成一片。
这户人家的主人叫陆波才,他的妻子叫欧秀英。傈僳族的话我听不懂,这两个名字还是陆波才在我手掌心比划几下才弄明白的。也幸亏这个陆波才和他的妻子还懂汉族话,此后的许多场合下,陆波才还当了我的翻译。
陆波才今年40岁,欧秀英今年35岁,都是祖祖辈辈居住在怒江大峡谷的傈僳族人。令人惋惜的是两口子至今没有孩子。陆波才说,曾经怀过两次,全流产了。后来担心欧秀英的身体,不敢再怀了。我问他没有孩子以后怎么办,陆波才说,没想过,眼下只能这样。

聊天的人们准备吃饭了。我的口福就这么好,不用找饭,饭就来了。不过,虽然已是午餐时分,可这餐饭还是早饭。陆波才说,今天上午一直忙着杀猪,早饭还没吃呢。
欧秀英在院子里摆上一张小方桌,端上一大盆煮好的猪肉,再别无它菜。
吃着肉,喝着汤,扒着饭,第一餐傈僳族的饭菜让我很惬意。坐在我旁边的陆波才提示我,现在不要多吃,等会儿还有好吃的。
我有些纳闷儿,正餐还不是好吃的吗?还有什么比正餐更好吃呢?
简单地吃过“早饭”,我就直奔主题,问陆波才家里是否能够借宿。在一个傈僳族人家吃住两天是我怒江之行的重要内容,寻访经验告诉我,只有住下,才能深入。
听说我想在他家里住两天,感受一下傈僳族的日常生活,陆波才二话不说,爽快答应,给我的感觉似乎连想都没想,还特别强调吃住免费。
陆波才家的那栋平房有三间房。中间一间相当于客厅,摆放着沙发、电视机柜以及其他用品。左右各两间住房。可能是落实农村养老政策,政府出钱为他的父母亲在旁边盖了两间小房,原来老人们住的房子正好空着。
欧秀英马上清理很有些杂乱的房间。清走床上的杂物,衣柜里拿出干净的铺盖。一会儿工夫,床铺好了。我特地拍了几张照片放在朋友圈里,并说明这是我在陆波才家的住房。
终于安顿下来了。我坐在床上,打量着这间房,今年春节就在这户人家过了,这两天就要在这张床上打滚儿了。这一切好像都发生在不经意之间。
我默默地想,寻访原生态少数民族风情,没有很强的环境适应力,一切无从谈起。

下午3点多钟,陆波才说的“好吃的”开始了。
欧秀英搬出一个架着四条腿的长盒式铁炉子,又把一块薄薄的铁板洗刷干净后放在铁炉上面,然后在炉膛里生上火。接着又搬出一个过去洗澡盆大小的不锈钢盆子,里面装着大半盆切好的肉、火腿肠、豆制品、土豆片、笋瓜片等。
欧秀英把切好的猪肉等食材放在铁板上开始烤制,陆波才则招呼着人们开吃。陆波才告诉我,这是傈僳族的吃烤肉,平时很少吃,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杀猪吃烤肉,来吃烤肉的都是自家的亲戚和很好的朋友。吃烤肉很随意,没有量的限制,只要你吃得下;没有时间限制,只要你还想吃。
我看明白了。首先是因为过年,大家才在一起吃烤肉。
吃的方法相当于自助式的烧烤。你既可以坐在炉子边守着吃,也可以端着碗溜达着吃,还可以歇会儿再接着吃;你可以直接吃炉子上烤熟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另烤自己爱吃的。这种吃法场面大,随性,随意,完全是那种“大块吃肉”感觉。
熊熊的炉火映衬着黑红的脸膛、铺满铁板的食材、烤得“滋滋”作响的肉块、大快朵颐的吃相……豪气难当的傈僳族吃烤肉,应该是、必须是傈僳族原生态民族风情的一道风景线。
大块吃肉,应该也大碗喝酒。但是,这里的傈僳族群众的信仰,让他们不抽烟,不喝酒。对汉族同胞来说,如此豪气的场景没有美酒,真的是差了一点什么,甚至还觉得不可思议。但眼前的傈僳族兄弟姐妹,什么都不喝,充其量喝点饮料,一样吃得酣畅,酣畅的淋漓尽致。
吃烤肉的人们有的走了,有的又来了。吃烤肉像流水席般一直持续到晚上。

陆波才告诉我,他有兄弟姐妹6个,因为他的父母亲跟着他,今天他家吃烤肉是他们家族团聚。明天(腊月三十)兄弟姐妹都回各个小家团聚。
吃完晚饭已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接着,陆波才又带我去怒江边沐浴,混浴。(这两个活动将专题呈现)
从怒江沐浴回来已快腊月三十的凌晨一点了,身上有些发热,我站在院子里享受着微微的江风。
我喜欢怒江大峡谷的夜幕。这不仅仅是因为非常少见的满天繁星和星光下起伏的山影,更因为夜幕可以掩饰一些尴尬。
和其他傈僳人家一样,陆波才家没有厕所。陆波才说,傈僳族之所以家里没有厕所,是因为气味太大。他告诉我,如果是白天,大小便都要去下面的公共厕所。晚上嘛,只要不让别人看见就行。
人有三急。白天去小了两次,气味刺鼻,而且难以下脚,每次都屏住气息,匆匆完事。终于,夜幕降临。小试一把,感觉真是方便多了。原来还有些担心的半夜如厕问题也随之而解了。
同样的尴尬在陆波才的二姐家也曾遭遇,所不同的是,不用去外面,在她家的屋后,极其简陋的厕所和猪圈连在一起。看那个架势,人和猪的大小排泄物直接排在了岸边的石头堆里。如果怒江水位抬高,这些排泄物的去处不言而喻。
这是在傈僳族山寨不得不说的一种体验!
农历腊月三十。傈僳族山寨仍然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生态节奏。已是北京时间8点,而大岩房才在此起彼伏的鸡鸣和猪圈里的猪叫声中慢慢醒来。
腊月三十早上,欧秀英一起床就忙开了。清扫冲洗院子的地面,洗刷昨天吃饭的锅碗瓢勺,给猪圈里嗷嗷叫的9头猪喂猪食。这是一个勤劳的傈僳族女人。
陆波才递给我一块芭蕉叶包着的食物,说这是傈僳族的糯米粑粑。早上先吃一点,一会儿下山,去他二姐家。他二姐家今天杀猪,去吃烤肉。
陆波才的二姐家在山下的怒江边,紧邻那座跃进桥,距大岩房村约2公里。昨天,二姐一家四口人应邀到陆波才家吃了烤肉,今天他们家杀猪,回请陆波才两口子吃烤肉,我也顺便有了口福。
二姐家杀的是一头不大的“双排扣”。傈僳族习俗,只有在过“阔时节”时才杀大猪。我们到他家时,有点血腥的“杀”的过程刚刚完成,正在火烧退毛,接下来就是开膛破肚,再按部位分解。我拍了一些照片和小视频留作资料。由于过程还是有些看不下去,就不做描述,也不展示了。
吃烤肉的流程与陆波才家大同小异,只是不像陆波才家有一个烧柴的长方形盒式铁炉子,而是三块长条砖搭成一个灶,上面放一块长条形石板。烧火把石板烤热,上面就可以烤肉和其他食材了。
一边吃烤肉一边聊天。陆波才的二姐夫叫叶南付,1979年2月18日出生,今年39岁。二姐陆波英,1976年3月出生,比叶南付大3岁。汉族有句话叫“女大三、抱金砖”,不管傈僳族是不是这个道理,反正陆波英比叶南付大了三岁。
别看这小两口年纪轻,生起孩子来可不含糊。他们有3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儿,今年21岁,前两年出嫁了。大儿子今年16岁,小儿子今年8岁。
叶南付的女儿很快就要当妈妈,他马上也要当外公了。不到40岁就当外公,这让我大吃一惊。再一想,人家16岁就已经结婚,不到40当外公也就不奇怪了。

从陆波才二姐家吃午饭返回,路过怒江边的 “登埂澡塘”,路边有一溜为那些“澡客”服务的摊点。两口子进到一家卖傈僳族服装的摊点,分别拿起男女装看了看,在身上去比划比划,陆波才还套在身上试了试,又出来了。看表情,他们很喜欢自己的民族服装。
在陆波才的印象里就没有穿过本民族的服装,欧秀英记得是小时候穿过,还是和姐姐共用,这么漂亮的傈僳族服装从未见过。他们有很久没穿民族服装了,家里也没有了。
我动了恻隐之心。我和傈僳族女老板阿娜聊了聊,问了问价格,男装上衣200元,一套女装600元,头饰另算350元。对于平时基本上没有什么现金收入的陆波才和欧秀英来讲,价格的确是贵了一点,花几百块钱买一套衣服想都不敢想。但站在这位女摊主的角度一想,她也不容易。这些民族服装很多工序是手工,有的还是绣品。这些衣服当地群众几乎不会买,外地游客即便要买也是少之又少,不如一起关照一下。我和摊主一商量,1000元搞定。
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把两口子惊呆了,拒绝的态度和话语可想而知。我给他们做工作,让他们接受。两口子高兴坏了。陆波才把刚才看中的衣服立刻穿上身,欧秀英则在摊主的帮助下,挑了一套自己喜爱的衣服穿在身上试了试。
回家的路上,穿着新衣的陆波才碰到熟人就比划自己的新衣,还指指我。回到家里,欧秀英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马上换装。穿上新衣服,欧秀英特地到父母的房里去了一下,还特地到寨子里走了一圈。回到家里时后面还跟着两位热心观众。欧秀英说,大家都说衣服漂亮,我这几天要天天穿。
穿上新衣服的两口子主动对我说,我们从没有照过相,更没有一起照过合影,你能不能帮个忙。听到这里,眼眶有些发热。还说什么呢,必须的。
两口子穿上新衣服后的高兴劲儿让我很意外,我似乎从中悟到了一点什么。
办好这件事儿,还得感谢一个名叫“金湖湾”的文化企业。从2018年开始,这个位于汉口江滩三期的“金湖湾”成为我《走进五十六道门》途中公益活动的坚强后援。
腊月三十的晚餐是在陆波才的妹妹家。下午从他的二姐家回来,欧秀英对我说,你先在房间休息,我们去妹妹家帮忙,饭熟了再来叫你。
我倚靠在床头上,把头脑里的文字记录整理在手记本上,过程中又打了个盹儿。迷迷糊糊中,欧秀英把我叫醒,吃饭啦。

是不是年夜饭,是不是团圆饭,我不知道,但参加的人员又应该是团圆饭。主要宾客是“4+1”,陆波才和欧秀英、陆波才73岁的父亲和70岁的母亲,还有我。主人家是陆波才的妹妹和妹夫两个女儿。
一张小方桌(傈僳族人家就没有大桌子)上摆着几个盛菜的锅碗。菜不多,远不像汉族团圆饭桌上那么丰盛。但对傈僳族群众来讲,这是一桌高水准,都是硬菜、狠菜。一锅怒江鱼,猪肉焖藕,猪肉炖萝卜,炖鸡,而且猪肉焖藕、猪肉炖萝卜还各自添了两碗。桌上竟然还摆着一盘北方饺子。
从食材的来源上更可以看出陆波才妹妹家对这餐饭的重视。鱼是从怒江里打捞的,猪和鸡是自己家养的,但藕、萝卜、饺子是买的。他们平时买东西要到10多公里外的六库镇,来回车费就要20元。
因为傈僳族一般是不过汉族春节的,所以晚餐的仪式感也不强。除夕的这餐饭还是没有酒,傈僳族群众信教,不抽烟不喝酒;还是习惯的做法,一人一罐“王老吉”。没有祝福话语,没有举杯碰杯,自己喝,自己吃。满桌子的人,要么不讲话,讲话只有一句话,而且全部是对我讲:“吃吧,多吃点儿。”
春节期间没酒喝,这可是第一次。忍着,回武汉补课。
2018年春节,多年来第一次没和家人在一起。但是,半山坡上的大岩房村;崖上人家的木板床;只能“大块吃肉”、不能“大碗喝酒”的傈僳族烤肉;埋头苦干、没有仪式感的除夕晚餐;夜晚在山村教堂想起,飘逸在怒江峡谷上空的天籁之音。夜幕下怒江边的混浴;朴实真诚的傈僳族兄弟姐妹,原生态的傈僳族民族风情……,这个春节,注定让我难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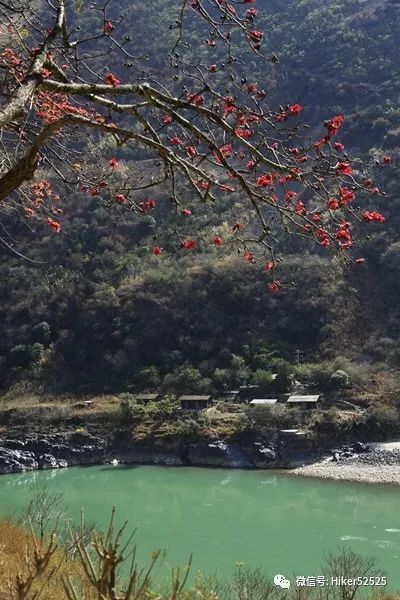
(编者注:本文较作者原文,略有删减)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