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琰娇
自从步入自媒体时代,大众文化的流量生态就越发明显,轰轰烈烈的“造词运动”让人不得不时刻紧握手机不断刷新,以免掉队。然而近时流行的“佛系”却恰恰与积极的网络生态相反。作为一种事事不必走心的生活方式,“佛系”原本不过是一碗普通的心灵鸡汤,凡事看开点,饿了煮碗面。之所以能够走红,并不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值得争议,而是因为出现了“佛系”倒挂,本该积极向上的祖国花朵纷纷称自己为佛系少女、佛系少年,甚至“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
我们既可以说“佛系”是新自恋主义的表现,也可以反过来认为“佛系”是对过于积极的网络生态的想象性抵抗,但用苏珊·奈曼的眼光来看,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根本。“佛系”的实质是青年人过早老成,跳过成年人的责任直接“享受”老年人的洒脱,错位的背后是青春与社会的矛盾。
在《为什么长大》这本小书里,苏珊绝大部分篇幅都用来向我们描述成长的困境,与其说书名叫“为什么长大”不如说是“为什么长大如此困难”。在她看来,长大的核心是鼓起勇气,独立判断,而事实却是,我们在接受常规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打破常规的能力。因此,理想中的“成长”和现实生活中的“成长”从根本上就是矛盾的,这也是成长困境的根源所在。
在苏珊看来,解决成长困境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启蒙。什么是启蒙呢?举个例子,启蒙所造就的判断力不是选择用哪个APP点哪种外卖这种小决断,而是能否思考外卖生态对整个环境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一方面,外卖会给环境造成额外的污染,但同时外卖产业也会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启蒙需要我们思考如何面对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如何走向一个更合理的世界。
但当下的教育模式却问题不少,我们对成长的理解也常存误会。我们总把青春期看做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大加赞赏,而事实上,这一阶段恰恰是人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大部分人在学校学习的内容和就业从事的工作几乎无关,步入社会之前过度被保护,初入社会之后压力重重,二者之间几乎没有过渡。大家在学校还心存理想,可真到就业的时候早已无暇顾及,到哪里去找一份真正“有意义”的工作呢?既然没有真正“有意义”的工作,不想长大也就不足为奇了。“佛系”青年不过是不想长大的中国式彼得·潘。
无论是重读卢梭、康德、休谟,还是波伏娃、阿伦特,苏珊都没能给出一个理想的教育模型,教育是一个既复杂又很容易产生偏差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珊强调了哲学的意义,哲学的最大任务就是拓展我们对可能性的感知,让我们学会面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为什么我们不想长大?因为长大比想象的要难太多。“听话”和“独立思考”之间的关系总是摇摆不定,朋友圈热点追踪已经在代替我们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我们从小熟知的“长大了就懂了”“长大了就好了”的教诲也很有可能是对成长的误会,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也未见得就一定是好事。
人应当如何成长,是一个值得反思却常常被忽略的问题。社会越进步越需要反思,越反思越感到脚下步履沉重。长大从来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它需要我们在生活的挫折里形成判断,打破常规,寻找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长更多地关乎勇气而非知识,因为知识无法代替勇气。
自然,苏珊的看法未必都对,但她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成长的书单,由此让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自己,重新观察生活。而不想长大,也未必就是幼稚,正如苏珊所说,成长本就是“一场永无休止的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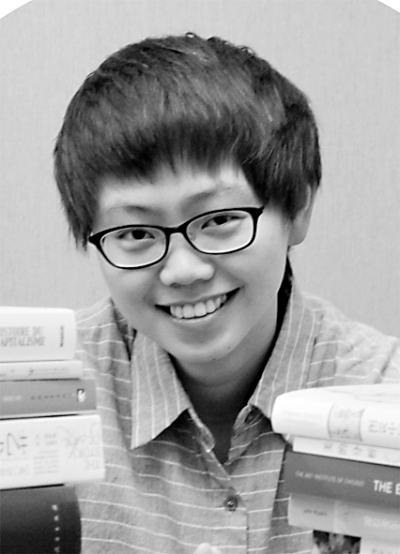
陈琰娇北师大文学院博士后,从事文化研究和电影批评。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