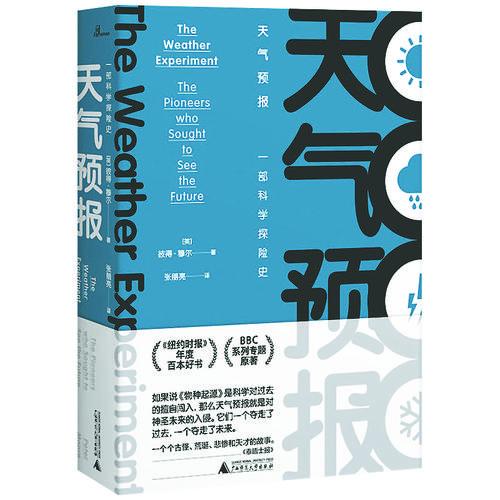
长江日报记者 黄亚婷
刚刚过去的周末,武汉人因为未能如期而至的大雪,又调侃了一把天气预报,这种调侃,每逢初雪、暴雨之类的重大天气前后都会上演数遍。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有漫长的岁月是依靠神话、农谚揣摩“老天爷”,而科学意义上的“天气预报”,其实19世纪之后才慢慢发展起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的新书《天气预报》,讲述了1800年至1870年那段长达70年多年的天气预报开拓史,现代天气预报的发展,远比普通人想象中的要复杂艰难,它伴随着神学、航海、战争等,开拓者们包括航海家、发明家、天文学家、工程师,甚至画家、数学家、冒险家……
从“天堂”到大气:
19世纪最大胆的科学实验产物之一
时间推至19世纪前,科学的天气预报尚未出现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本书作者彼得·穆尔举了一个典型例子。1703年11月24日下午,置身于风和日丽天气之下的人们不曾想到,英国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大风暴正在狼奔豕突般朝英国的西海岸涌来。人们对于汹涌而至的风暴毫无防备。最后,大风刮落了教堂屋顶的铅制窗框,风车飞速旋转,以致最终像巨大的转轮烟花一样燃烧起来。牛羊被刮得四散奔逃。虽然没有最终明确的伤亡记载,但事后人们预计,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约有1万人因这场风暴遇难。彼得·穆尔还描述了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英国“小说之父”对这次灾难的态度,“在丹尼尔·笛福看来,这次大风暴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了英国伦敦的大火灾”。
认识到极端天气的危害,却对此束手无策,19世纪之前的漫长岁月里,绝大多数人将天气视为一种神力,是上帝弹奏的背景音乐,用来预示某种变化或惩治罪恶,古希腊神话里的“众神之王”宙斯手持闪电,太阳则是被阿波罗赶着马车每天拉进拉出……当风暴来临时,人们只得寄希望于“神力”,基督徒会敲响教堂的钟声,并伴随牧师们的祝福,希望以此来祛散恶劣的天气。
彼得·穆尔在《天气预报》中并未纪录中国,但中国神话体系里的雷公、电母、风婆、龙王,也是祖先们对天气无法解释而展开的“某种神秘力量”想象,尽管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农耕劳作中,总结出了二十四节气和无数农谚,可这些经验总结并不能替代科学的天气预报,人们始终把天气视为“老天爷”掌握的某种特权,向上天祭祀、祈求风调雨顺是农耕时代的重要社会活动。
从混沌无知到科学认知,对天气现象的解读存在巨大难度。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人们提出了各种理论。但少数分散在各地、坚持对气温和气压进行观测和记录的研究者们,缺少的不仅仅是标准的科学用语,同时也缺乏一个用来分享其研究成果的端口或平台。每个人所在的地域范围都是有限的,只能对各自地区的天气特征有所了解,却对宏观的天气形势缺乏总体认识。他们对锋面、气旋、积云、温度垂直递减率、辐射流等概念一无所知。
直到1800年,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在科学界,“大气”(atmosphere)这个词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该词属于希腊语的复合词,表示的是四周的水汽。这种语言学上的转变也反映了科学界立场的一种变化。与天堂不同,大气和人的心脏、植物的花冠、砂砾岩一样,需要进行理性的分析。亨利·卡文迪许、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和卢瑟福分别发现了空气的主要成分——氢气、氧气和氮气,这使得人们对四周漂浮的空气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1800年至1870年那段时期,一群背景各异的人决定向“上帝”讨要天气解释权,他们创立了基础理论,发明了实验仪器,建立起观测网,并试图说服政府部门。1802年,霍华德发表了《论云的形变》,首次以科学的名称给云命名。若干年后,弗朗西斯·蒲福提出了量化风级的观点。1823年,约翰·弗雷德里克·丹尼尔的《气象学随笔》问世,再次引发人们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兴趣。到19世纪30年代,气象相关的文章和报告见诸各种科学杂志,各种气象学会和天气观测者网络也纷纷建立。更多成就随之而来:出现了第一份天气图和最早的天气报告,人们对露水、雪花、冰雹和风暴也有了新的认识。人们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研究大气现象,天气预报也成为19世纪最大胆的科学实验产物之一。
从船长到“近代天气预报之父”
本书以罗伯特·菲茨罗伊船长的故事作为各章节之间的巧妙串联,还生动刻画出了苛刻的官员、吝啬的政客以及疯狂的发明家等人物。被视为“天气预报创始人”“天气预报之父”的罗伯特·菲茨罗伊,是著名的“小猎犬号”的船长——达尔文曾乘坐此船进行远洋航行,菲茨罗伊还是英国海军中将,水文地理学家,气象学家,1854年成为英国气象局局长。
书中讲述的菲茨罗伊船长,性格复杂而矛盾,充满了豪情壮志。他早期曾探访过火地岛,后来在英国政府任职,全心投入天气研究。在同时代的人中,菲茨罗伊是一个佼佼者。他迫切地想通过自己的研究造福世人。他的这种立场在当时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同时也给他四处树敌,被指责为“鲁莽、狂妄和盲目自大”。
但菲茨罗伊始终相信,他是在顺应时代的发展。到19世纪50年代,气象学家不再是受到孤立的群体,他们建立起越来越多的联系网,通过电报这个新技术来分享观测数据。电报的发明、气象理论的发展,以及众多坚持不懈的人物前赴后继,形成强大合力,致力于证明地球大气不是混乱而不可捉摸的,相反,人们可以研究它、理解它,并且最终对它进行预测。直到1861年,英国第一份全国性天气预报正式发布,当时人们采用了一个新词:(天气)“预报”(forecast)。
1870年之后的故事,《天气预报》没有继续讲述,但正是1800至1870年的不断开拓,后来者们才有了用科学眼光审视天气的可能性,天气预报的重要性也逐渐被大众认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天气预报之一,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英国停止了播报天气预报,因为当时信息传递不及今天便利,并不是人人都能轻易获取天气信息,天气预报成为事关作战成败的军事机密。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发生根本变化的诺曼底登陆,盟军必须找到最适合登陆的那一天。为此,一批英国和美国的气象员组成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气象委员会,并很快得出推论:从冷气流通过到低气压云团来临前的这段时间,英吉利海峡的天气将好转,这一天很可能是6月6日。最终,100余万英美盟军部队在6月6日开始登陆诺曼底,开启了二战中西欧战场的大反攻。
《天气预报》的中文译者张朋亮说,天气预报的由来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很多,这不仅在于天气现象本身的复杂、宏大和瞬息万变,同时天气研究也面临着古老学说、守旧思想和宗教信条的多重牵制,当我们习惯性地把天气预报当成生活的重要参考时,不应忘记,曾经有那么一群人为此苦心孤诣,倾尽一生,而跟随彼得·穆尔的独特视角,重温这段给自然以秩序的光辉历程,显得尤为重要。他还表示,要想读懂风霜雨雪这种天书般的语言,只靠聪明才智是远远不够的,更多时候是需要默默坚守、奔走呼号,动员足够多的资源来建立与天气现象等量级的研究机制。
【读书旁通】
历经战乱,防御特大洪水立下奇功
你应该知道的武汉百年天气预报开拓史
长江日报记者 陶常宁 黄亚婷整理
除了从《天气预报》中探寻世界天气预报开拓史,你还应该了解武汉的百年天气预报开拓史,要知道,武汉可是中国最早建立天气预报系统的城市之一。根据武汉市气象局发布的消息,今年6月,武汉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获得认定,已经入选首批“中国百年气象站”,是获得“百年认定”的十大气象站之一。
殖民与战乱中夺回自主权
武汉市气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武汉最早的地面气象观测始于1869年(清朝同治八年),观测地点在汉口海关(即江汉关,现称武汉关)。
那是一段伴随着屈辱与黑暗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求,要求在中国沿海和长江沿岸开埠地设立气象机构。1862年,汉口海关成立。根据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的提议,汉口海关于 1869 年建立气象站。但当时的观测站并不具备天气预报能力。 在1880年以前,汉口海关的气象观测项目为:日最高和最低气温、9 时和 15 时大气压力、降水量和降水时数、中午水位及其 24 小时涨落、24小时盛行风向及其风力等。观测人员也来自英、美、法、俄、日、 德、意等国,直到1913年后,才有中国人参与。
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始自办气象事业。1929年9月,汉口特别市社会局在汉口中山公园建立气象测验所,当年10月开始观测。国民政府于1929年11月在武汉大学建立测候所。抗战爆发后,测候所随武大西迁四川,气象观测一度中断。直至抗战胜利,才恢复珞珈山观测站。另一方面,1936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与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创设武汉头等测候所,1938年,武汉空袭警报频繁,测候工作随之中断。抗战胜利后,1947 年 1 月恢复。1948 年初,武汉头等测候所改隶中央气象局,升格为汉口气象台,并成为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区台”,汉口测候所也并入该台 ,1948 年12月,汉口气象台开展天气预报工作,但仅一个月左右便停止。
抗洪救灾,重大活动的“指南者”
武汉解放后,武汉气象观测翻开新的篇章。1949年6月,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航空组接管了汉口气象台和汉口王家墩空军机场气象台,合并为汉口气象台。1960年1月,汉口中心气象台的地面、高空观测业务迁至东西湖区吴家山,称为湖北省气象局汉口中心气象台,1982年3月改称湖北省气象局观象台,后改由武汉市气象局管理。
东西湖吴家山观测站第一任工会主席和第一任观象台台长,已是90高龄的赵在田回忆:搬迁至吴家山之前,观测站紧挨铁路,环境相当嘈杂。观测站里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大家除了值班,还要去农场参加劳动,尤其三年困难时期,大家只能靠种植南瓜来填饱肚子。
作为两江交汇的重要枢纽,武汉的气象观测在抗洪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4 年是湖北特大洪涝年。那年,武汉关的最高水位达到了 29.73 米,是当时有水文记载以来的最高水位。 汉口中心气象台集中骨干力量,并首次与中央气象台(时为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开展天气会商。 1998年夏天,长江发生全流域大洪水。当时,观测站楼梯顶不断漏水,大家每次进出都要披着雨衣,冒险蹚水。那时,市气象局与市委党办系统综合信息通信网已经开通,每日的气象信息、观测实况等都要直通市委、市政府,宝贵的观测数据为抗洪救灾提供了有效决策参考。
1980年,武汉气象站被定义为国家基本站,2013年7月更名为武汉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如今,全市高分辨率、自动化的综合气象监测网初步建成,自动气象站网布局达到5公里间距分布;开发综合气象观测业务平台,实现了地面观测自动化、高空和地面观测一体化、实时和历史资料一体化;完成了雾霾天气监测、极轨卫星遥感监测等系统建设并投入业务运行;在城运会、马拉松等重大活动,以及持续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等重大天气灾害时,为社会提供优质气象服务。
尽管以目前的人类学识,天气预报还不能实现百分百准确。“湖北天气”官方微博也就上周未能降下大雪作出解释,“天气形势是不断变化的,预报结论也会相应的做出改变,我们能做的,是不断根据最新的天气形势,订正预报,让它越来越准确”。
从1800年开始,天气预报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人类从“老天爷”手中拿回的这份天气解释权,还只是一知半解,比起吐槽,对待这门自然科学,或许更应该如开拓者们一般,抱以足够的勇气和耐心。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