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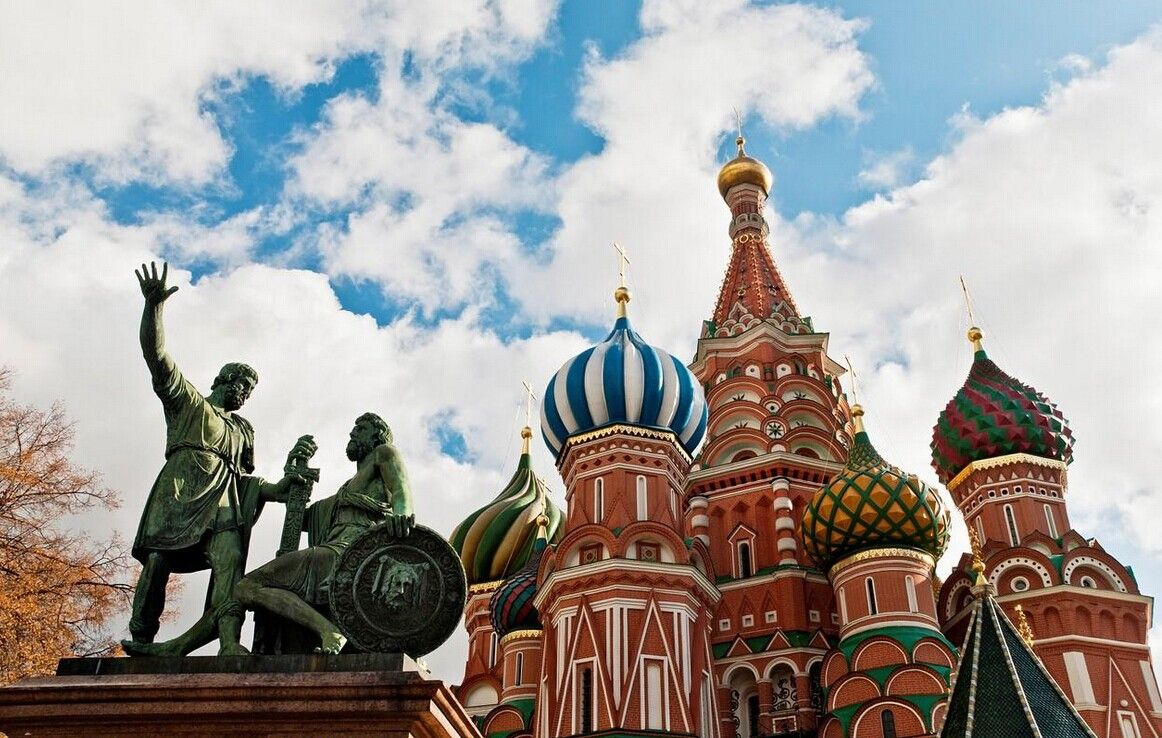 俄罗斯
俄罗斯
在离窗一步之遥的地方,他掸去斗篷上的毛发;他指着冰峰起誓:“睡吧,亲爱的,我必如雪崩再来。”——帕斯捷尔纳克
冬天晚上,最美好的事情是:蜷在被窝里看书,喝滚烫的水果茶,整夜整夜开着音箱听音乐。老柴、斯克里亚宾、拉赫玛尼诺夫、鲍罗丁……艺术,在他们这里是个严肃的问题,涉及民族骄傲、宗教、历史、隐秘事件、崇高、良知、忧郁。因此,他们的音乐本质上都表现了一种大绝美与大凄怆。这样的意境对应时节,与屋外寒天冻地里的松涛合唱缱绻重叠,顷刻便拥有无限延伸和层层探入的乐意空间。世间沉暗,曲动流年,不可言说的深邃美感,像哑了喉咙的俄罗斯,又温柔又粗野。
良夜迢迢,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先来自格林卡的民歌和管弦乐幻想曲,原文演唱的词韵当真是“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歇”,浪漫音符燃亮那只蜂蜜味道的蜡烛,香气很淡,饱满如浆果般的光宠让花朵落满我们的河面。若手边正读一册《三人书简》,茨维塔耶娃1922年诗中的无手之握,无唇之吻,及与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之间的情爱河床倾溢载满贪恋。民间曲调素材迤逦出水中星月之象:“河流后退的世界,岸上也是河流。一只虚妄的手,握住了另一只手的虚妄。”
中提琴悲歌与大提琴奏鸣,将我们从温暖地域带出,带到旷野,或远方的名城。
风寒,街阔, 垂暮冬日弥雪,行板乐章忧郁而彷徨,孤寞震灼,浩荡冥想,犹在坚刃翻覆的潮浪之中不愿意抽身。乐句是面对孤独的勇气,音乐是最可以说服人的东西。如果阿赫玛托娃的缪斯沿着山道离开了,如果托尔斯泰开口讲话,我想就是这样的嗓音。他们割草、做靴、锄地,书房的桌上,摊着《卡拉马佐夫兄弟》……
钢琴琴键如犁铧敲开冻土, 深埋,战栗,槌槌和弦翻耕着民族的血痕。
历史是这样的鲜活疼痛,延缓不止。揣想作曲者试图用诸多协奏曲的编号来历数广袤云天下的家国民众庄稼湖泊。战火浮生,所映照的天光是踏板下的延长音,使之人性茫然,没尽头似的。
艺术和真实就这样无奈的交叉,更应了哲学家塞内加那句话: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
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抒情旋律连线,主题既出自艺术家们的灵感源泉,也同样依靠着以下这些高贵的名字:普希金、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维坦、肖斯塔科维奇、屠格涅夫、列宾……他们的人生交响配器《帕斯捷尔纳克》诗中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弥撒曲震颤中相逢的灵魂;布罗茨基在1987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掩面而泣,他说:“俄国的文明已经结束;如果我要说它是以悲剧结束的,那么首要的依据就是人的牺牲的数量,已降临的社会和历史转变将他们掳掠而去。真正的悲剧中,死去的不是主角,死去的是整个民族合唱队。”
诸神赐予合唱队员们下落不明的生活,艳丽如血,万千彤云。而民族的痛哭被编成乐章,留给世界的记忆如此刻骨铭心!
 徐戈
徐戈
徐戈 长笛教授,音乐专栏作家,微博名dolce小裁缝。【编辑:袁毅】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