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记者袁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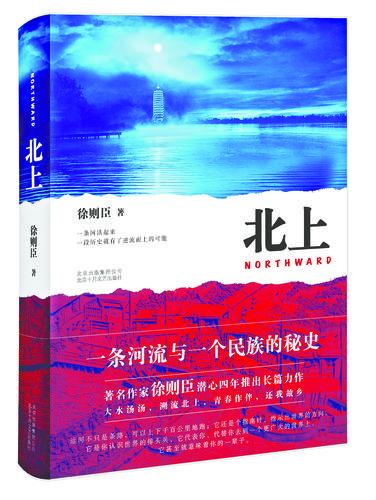
“水和时间自能开辟出新的河流。在看不见的历史里,很多东西沉入了运河支流。水退去,时间和土掩上来,它们被长埋在地下。2014年6月,大运河申遗成功前夕,埋下去的终被发掘出来。这是京杭大运河济宁段故道近年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著名作家徐则臣在长篇新作《北上》开篇中,写下如此意味深长的文字。
2014年,大运河申请世界遗产成功;2014年,徐则臣重走1797公里的大运河。2018年12月,徐则臣耗费四年写成的《北上》问世,与李洱《应物兄》、石一枫《借命而生》、徐怀中《牵风记》、梁晓声《人世间》一同入选“《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这一年,徐则臣40岁。
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
《北上》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 1901年,为了寻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失踪的弟弟,意大利旅行冒险家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了中国。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他走访,召集起各种底层人士一路相随。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
这一路,既是他们的学术考察之旅,也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反思之旅,同时,更是他们的寻根之旅。当他们最终抵达大运河的最北端——通州时,保罗•迪马克因意外离世。同时,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运河的实质性衰落由此开始……
作家徐则臣力图用30万字跨越运河的历史时空,探究普通国人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书写出一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出版该书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称:从这个意义上看,《北上》既是一条大河的故事,也是民族与文化的故事。
徐则臣在《北上》扉页中有两段献词,一段是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之八十三:“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二段是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话:“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这两段献词,正是这个国族的国运和这条运河的河运注脚。
所以《北上》之“北”既是地理之北,亦是文脉、精神之北。这个民族的“秘史”与旧邦新命,徐则臣都付予了眼前这一条大河。
大年初六,在接受长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徐则臣说,做了大量案头工作和田野考察,他才把大运河作为主角推到小说的前台来,这次倾囊而出,再现了上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浮世众生相,“虚构不是瞎写,更不是乱写和随便写。”
大运河边上的花街
徐则臣16年前写了第一个关于花街的小说《花街》,就打算以此为名出一本主题小说集,去年他自选了九个故事作为中短篇小说自选集《花街九故事》。这是撕扯在乡村和城市,搁浅于往昔与未来的九个故事,承载着由人生悲喜与人情温凉汇聚而成的大运河……
“从运河边上的石码头上来,沿一条两边长满刺槐树的水泥路向前走,拐两个弯就是花街。一条窄窄的巷子,青石板铺成的道路歪歪扭扭地伸进幽深的前方。……临街面对面挤满了灰旧的小院,门楼高高低低,下面是大大小小的店铺。生意对着石板街做,柜台后面是床铺和厨房。每天一排排拆合的店铺板门打开时,炊烟的香味就从煤球炉里飘摇而出。”生在花街,长在花街,人在花街,心在花街,这些出走的人、留下的人,他们的足迹都是花街的故事。在徐则臣笔下,花街俨然成为一条越走越漫长的街巷,并且正在成为世界。
为此徐则臣夫子自道:“当我闭上眼,看见从花街幽暗的街道上明亮地走出来的小说中,走在最前头的,就是这九个故事。”
花街系列小说一出手就为徐则臣赢得了广泛声誉,《如果大雪封门》《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青云谷童话》等佳作迭出,就获得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冯牧文学奖,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2015年度中国青年领袖”。 徐则臣的小说因此被认为“标示出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可能达到的灵魂眼界”。
徐则臣的创作脉络分为两条,一为北京系列,二为花街系列。北京系列写的是平凡人群像与生存矛盾的对峙,花街系列写的是平凡人群像撑持在命运的河流上,不动声色地老去。如他所说:“作家有两个故乡,一个在地上,一个在纸上。”运河边上的花街正是徐则臣的纸上故乡,在他的作品里,花街逐渐生长成一个辽阔的世界。
批评家李敬泽赞叹:“他对充满差异的生活世界具有宽阔的认识能力,对这个时代的人心有贴切的体察”;“他对小说艺术怀有一种根植于传统的正派和大气的理解,这使他的小说具有朴茂、雅正的艺术品格。”
大运河的历史逆流而上
2019年是徐则臣写作的第21个年头。在他的作品中蛰伏了20年的运河,随着长篇新作《北上》的问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愈加清晰的面貌。
在70后作家弋舟看来,《北上》的文学抱负一目了然。又一次,徐则臣雄心勃勃地调动起他所有的文学经验,将国族、江河、错综的历史与万丈的红尘聚拢于笔端,在一部长篇小说中倾尽其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飘摇,京杭大运河的千里逶迤,以时空之力保障了这部长篇小说内在应有的“长卷品格”,域外探险者与中国知识分子、底层人士的相遇深意别具,徐则臣在此种“简写近代史”般的格局下,展开着带有替两种文明彼此做出文学说明的努力,而其以创作实绩对文学“格局”的重申,对于“70”一代作家而言,更是富有显豁的召唤意义。
“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作家徐则臣在《北上》结尾时,写下这段文字,为他的小说主角大运河划上圆满句号。

[访谈] 通过可靠的细节把历史和现实还原出来
认知越来越清晰,疑问也越来越多,写作是一个全面梳理的过程
读+:什么契机下,触动你起意并决定创作《北上》——写作在你作品中蛰伏了20年的京杭大运河?
徐则臣:写《北上》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以运河为背景写了多年的小说,我对它越来越熟悉,对它的认知也越来越清晰,当然疑问也越来越多。写作是一个全面梳理的过程。有一天和朋友聊起大运河,觉得一条河呼之欲出,就决定写了。
从小生活在河边,初中时住校,到冬天,宿舍的自来水管冻住,我们就端着牙缸、脸盆往校门口跑。校门前是江苏最大的一条人工运河,石安运河,一大早河面上水汽氤氲,河水暖人。后来在淮安生活过几年,每天在穿城而过的大运河两岸穿梭,一天看一点,一天听一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对运河也知道了不少。因为对运河淮安段的见识与理解,成就了我的运河之缘,二十年来,绵延千里的大运河成了我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
日常中运河只是我的生活背景,背景很容易被忽略,只有当你真正开始思考、研究和写作它,它的意义才能凸显出来,而且越来越重要。
读+:2014年开始,你决定重走1797公里的运河,在写作上你越来越像个实证派,为什么写虚构的长篇小说这么注重史实和现实的“实证”?
徐则臣:一是我个人的写作习惯,“绝知此事要躬行”,心里才踏实。二是这条河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存在,我必须通过可靠的细节把它还原出来,可靠的细节从哪里来?实证。虚构不是瞎写,更不是乱写和随便写。
长城是刚的存在,运河是柔的存在
读+:大运河对中国人文化意义上的塑造有哪些?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又起到什么作用?
徐则臣:常有人说,中国地大物博,这从侧面也说明了不同地区的风俗文化差异特别大,长城以北是大漠,黄河和长江之间是最繁华的中原,长江以南又是蛮荒之地,这三块之间,无论是民风、物产、习俗,还是文化,差异都很大。差异大了,怎么交流,就需要一个贯通的桥梁,而京杭大运河就彻底把南北方打通了,还贯通了中国的几大水系,贯通了,才能更好进行文化上的交流。
文化上的另一个明证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加上《金瓶梅》,都跟运河有关系。为什么有关系呢?运河是当年的大动脉,运河附近是信息、文化、交流最发达、最集中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才能不断的融汇提升。《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先当年在扬州刻过《全唐诗》,林黛玉进贾府走的就是运河,《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就生活在淮安,施耐庵是如今的泰州人,罗贯中据说是施耐庵的弟子,他们都在运河沿线生活过。此外,明清很多大人物都产生在运河沿线的城市,比如绍兴、无锡、苏州、常州、扬州等地,像苏州、无锡、常州这些地方,随便一个街巷,都有进士甚至状元,运河边上信息发达、交通便利,有运河在,上京赶考也方便了不少,这些都会促进文化的繁荣,近现代更不用说了,比如周恩来、蔡元培、鲁迅、周作人、秋瑾等都是运河边上的人。所以,运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
读+:大运河对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与文化性格有着怎样的影响?
徐则臣: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中国没有形成向外扩张的侵略心态,这跟运河沟通南北有关系。通过运河,连接南北,中国在内部就实现了自给自足,所以没有形成扩张的文化,而且运河加强了南北方的沟通和交流、不同地区巨大的差异又让中国人具有了兼容并包的宽容心态。中国东西向有长城,是刚的存在,南北向有运河,是柔的存在,所以中国人性格里有刚柔并济的特点。而且中国地区差异这么大,运河贯通南北,也为各地区的交流、民族的融合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让中国成为一个融合的大一统国家。
读+:作为历代漕运要道,千百年来,京杭大运河对北京意味着什么?
徐则臣:一直有人说“北京是一座在水上漂来的城市”,北京从元朝到明朝水系都非常发达,像北京的很多地名里都带有水,比如莲花池、积水潭、万泉河等,原来的船能绕着北京走一圈,这都离不开运河的补益。此外,当年游牧民族蒙古定都北京,北京开始承担京都的功能,他们吃的粮食从哪里来?从南方来,当时一直有一种说法:苏湖熟,天下足。所以明朝的时候,政府下决心把整个京杭大运河疏通了,为什么呢?因为要靠着运河运送各种物资呢,尤其是先吃饱饭再说,没有运河,就没有粮食,没有粮食,北京城就没有存在的物质基础。
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
读+:你把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断续走了一遍,你看到了大运河现在的真实现状如何?
徐则臣:济宁以南还在通航,运送的也多是笨重廉价之物,济宁以北基本上断流,有些地方连河道都湮没不见了,难以想象曾有一条滔滔大河行经此地,观之令人心伤。但没办法,这就是现实。
读+:2014年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存在,大运河被誉为“古代文化长廊”“古代科技库”“名胜博物馆”“民俗陈列室”,你觉得,运河的“文化”意义现在可以进行怎样的开掘?
徐则臣:这些年走过的运河沿线,发现当地政府的力气多半花在硬件建设上,重建和装修运河古镇,打造游乐场和商铺。那些复古的建筑于当地和运河而言,仅有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古”字,你很难在那些“古”中看见与此地相对应的“古”。你看不见它们曾对该地产生过怎样的作用,尤其文化上的影响。古只是泛泛的旧,千篇一律的旧,而非对当地历史的有效还原。
经过这些地方,我常感到遗憾,在他们的文化带建设中,看不见此地运河史上曾出现的具有符号价值和代入感的人文景观。而这些独特的人文景观和史迹,理当作为细节融入到文化带的建设中,移步换景,总会见到诸多有效的提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一路认真走下来,你便理解了这一方运河岸边的人是如何走到了现在,又为什么只能走成现在的模样。运河文化带应该是一段高度浓缩的、与运河相关的本地史志与生活志。当然,这样一个“运河与人”的局地史志中,也有必要草蛇灰线地暗含一条京杭大运河之于整个中国的影响和意义。风物流转,人员徙迁,不管你有多鲜明巨大的局地特性,你也只是滔滔大河北上和南下间,一直在相融相合的有机一环。
我写作《北上》最大的想法是,如果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把运河各项功能唤醒,要完全恢复当年的样子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文化意义上去重新反思运河曾经起到的作用,然后结合我们的时代,重新发掘运河承载的文化功能。运河是一条河流,也凝结了一个民族的一段历史。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铭记运河,某种意义上是铭记中国的历史文化。于是,思考、探索大运河在新时代下的意义,变得尤为重要。

“70后”作家只是一个纯文学现象,而非文化的乃至娱乐现象
读+:“70后”作家,大多没有历史的包袱,历史也很少成为“70后”作家叙事的关注焦点。作为“70后”代表作家,你为什么选择大运河和运河的重大历史作为独立的叙述对象?
徐则臣:一个题材或一段历史是否重大,从文学的意义上我并不关心;只有这个题材和历史引起我持久的好奇和探究的兴趣,才可能与我的写作发生关系,而一旦发生关系,所有的题材对我来说都是重大题材,所有的历史也都是重大历史。写大运河,跟它是否重要没有必然关系,写它因为我熟悉它,而且迫切地有话要说。
读+:“70后”作家大多已人到中年,你除了是中国“70后作家的光荣”之外,你还是《人民文学》副主编,在你眼里“70后”作家在创作与生活上有哪些鲜明的代际特征?
徐则臣:“代际”在今天的文学批评里,已经成为一个颇受诟病的术语,似乎谈论它就意味着目光短浅,文学的抱负也变得可疑。但我依然坚持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科学和有效。既然一个作家能够区别于其他作家,一代作家就没有理由不能区别于另外一代作家,后者的区别是什么?代际。当我们要考察一代作家的写作,考察他们的写作与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代际”就是必要的放大镜和显微镜。有一个宏观文学史,也有一个微观文学史,无数的微观文学史是组成了一个宏观文学史。代际对应的即是微观文学史。70后作家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大部分都是闷头干活的沉默者,他们只是一个文学现象,而非文化的乃至娱乐现象。这可能导致他们的声音经常被忽略,但这恰恰是我对他们抱有信心和乐观的所在。文学需要一群能够充分沉潜进行思考和创作的人。这群人可能无法像父兄辈那样,肩负一段深重的历史,但他们继承了父兄的理想主义;他们身处喧嚣、市场和娱乐,又没有被早早地招安;他们身处变动不居的复杂现实,全球化又培养了他们宽广的视野和逐渐增强的问题意识;这些都足以让他们成为一个个独特有效的“这一个”,写出可以为自身正名的好作品。




请输入验证码